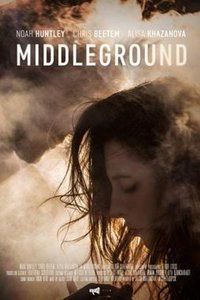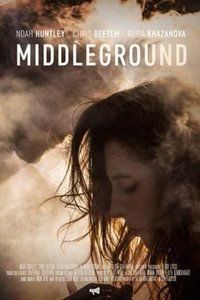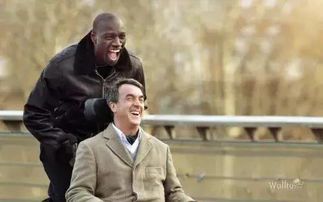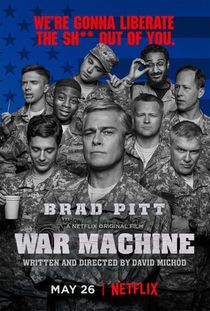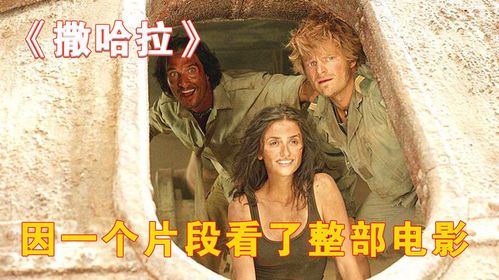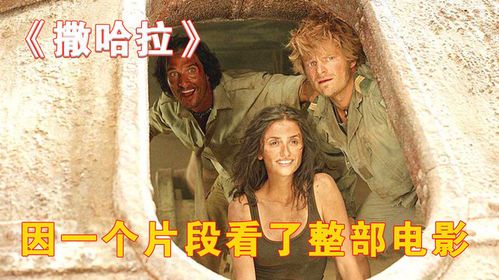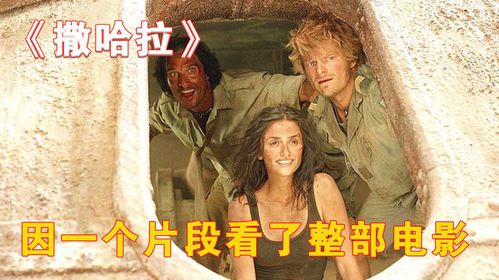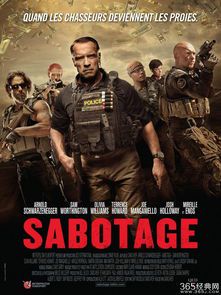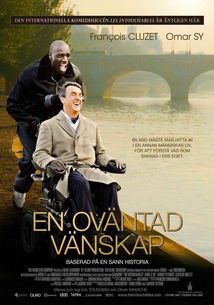你是否曾在影院黑暗中,突然被某个镜头击中?那感觉并非单纯的“这故事我听过”,而是更私密的震颤——仿佛银幕上的光影正从你记忆深处打捞未被承认的碎片。电影史学家克拉考尔称之为“现实的救赎”,当我们凝视《重庆森林》里过期凤梨罐头时,真正过期的或许是自己某段未被妥善封存的情感。
这种体验远比“既视感”复杂。伯格曼在《野草莓》中让老教授与年轻时的自己隔空相望,这种叙事技巧如今已成为心理惊悚片的标配。但真正令人战栗的时刻,往往是导演无意间复现了观众潜意识里的画面构图——王家卫镜头下潮湿的霓虹,或许正与你二十岁那夜便利店外的雨幕完美重叠。
神经科学给出过冰冷解释:大脑颞叶的异常放电会导致错误记忆。但电影学者蒂尔达·斯文顿说得更妙:“影院本就是集体癔症发作的场所”。当《盗梦空间》的陀螺在每个观众心底旋转,我们终于理解诺兰为何执着于胶片——那机械运转的咔嗒声,本就是记忆神经突触的拟音。
最吊诡的莫过于现实开始模仿电影。有人坚持认为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中暴雨洗罪的场景曾在自己梦中预演,而调查显示全球至少327人声称经历过《楚门的世界》式生活。这种反向的德勒兹“晶体-影像”,让柏拉图洞穴寓言有了赛博时代新解:我们或许早就是自己记忆电影的群众演员。
下次当银幕画面唤起莫名熟悉感时,不必急于归因。那可能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说的“偶然的恩赐”——电影与记忆在黑暗里共谋,为我们短暂地撕开了现实织物的裂缝。正如塔可夫斯基在《镜子》中呈现的:真正震撼的从来不是似曾相识,而是相识后的不敢相认。